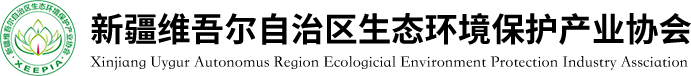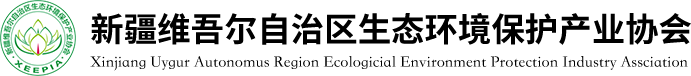资讯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电话:
0991-4165463
0991-4165461
0991-4165486
邮箱:
XEEPIA@163.COM
地址:
乌鲁木齐市南湖西路215号

新疆生态环保产业协会
江桂斌:新污染物研究“利应当着眼千秋”
中国环境APP / 2025-05-21 / :367
“新污染物研究应当以更高的格局,对标来自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外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国家需求。”5月17日,在第19届POPs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江桂斌在分享业界新污染物研究新进展后,勉励广大科研学者“新污染物研究功未必全在当下,利应当着眼千秋。”

图为江桂斌作大会报告
“收紧”定义,在治理中抓典型新污染物
在2024年11月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学术讨论会中,主要讨论了7个与新污染物有关的问题,“什么是新污染物?”是7个问题之首。
分享中,江桂斌再次回应了这一问题,认为当前应当严格新污染物的定义——新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
“新污染物要实现有效治理,定义不能过于宽泛。以往我们的定义大都是广义范围内的,但现在应当‘收紧’这个定义。要抓对人体健康、环境影响危害大的典型新污染物,否则的话是治理不过来的。”江桂斌说。
在他看来,新污染物一般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绝大部分来自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学产品,尚未有效控制其生产和排放;二是污染事件正在发生,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我们对其环境行为缺乏足够认知;三是毒理与健康风险的数据,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
他将新污染物分为化学类污染物,例如,绝大多数的POPs和内分泌干扰物,其中POPs是主体;生物类污染物,例如病毒、细菌和抗生素;物理类污染物,例如微塑料。
“但这三类并不是同样的重要,化学类还是其中的主体。”江桂斌表示。
新污染物不是定义得越“毒”越好
“科学的认知很重要,不是说新污染物把它定义得越‘毒’越好。”江桂斌指出,当前研究者对于新污染物的毒性研究要依据科学,实事求是。
2023年11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FOA类化合物列为Group 1级致癌物,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饮用水标准、工业、环境保护政策的重大调整。
江桂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PFOA的毒性和二噁英、PCBs(多氯联苯)、苯并(α)芘这些1级致癌物是没法比的。”江桂斌表示,IARC 的依据是一项为期两年的大鼠暴露动物研究, 人类致癌风险的确认并不在此研究范围内,而且研究中设置的暴露浓度高达300ppm,与现实环境中的PFOA赋存水平相差甚远。
“我认为,很多新污染物的毒性是普遍较低的。”江桂斌指出,这一判断并非有意降低新污染物治理的迫切性,而是要认识到,将来我们会长期面临更多的低毒性的化合物。
“只要存在有机污染物,它就有毒性,因为即使是低剂量的污染物,也有复合污染效应。复合效应的存在使得源溯与靶点锁定更加困难。研究中,由于方法不一样,追求一个绝对的毒性基准,没有太大的价值。”江桂斌指出,重要的是要通过标准来进行控制。例如食品中的全氟化合物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应当结合科学研究结果、有经济可行性技术支撑,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推出相应的科学标准加以控制。
在公共卫生领域,目前对于新污染物的研究非常火热。江桂斌提醒研究者,如何把对毒性的观测和健康联系起来,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是通过流行病学的角度切入,判断这种新污染物要限制,有污染,有毒性。但是怎么把观察和研究与人体疾病挂钩起来,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江桂斌指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方法的突破,虽然目前人工智能能给予一定助力,但也需要大量一手的原始数据来作支撑,否则研究容易陷入误区。
需要冷静对待微塑料“研究热”
从近年来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出版物《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简称ES&T)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新污染物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增速迅猛,其中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每年都在增加。按照四大类新污染物(POPs、微塑料、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来检索,中国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数量最多。
其中,微塑料的研究更加火热,在这一领域,中国在ES&T上的相关论文发表的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在近十年达到370篇,超出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
“我不反对研究微塑料,但是我们要将其置于一个很大的尺度去考虑,避免走进研究误区。”江桂斌特别指出,当下许多研究热衷于研究海洋动物及人体内的微塑料,科研工作者固然有发表文章的需要,但应冷静看待对微塑料的“研究热”,严谨分析微塑料的毒性。
不久前,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分校发表在《自然 医学》(Nature Medicine)中的一项研究指出,从捐赠者的大脑中分离出约10克微塑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江桂斌认为,这一研究的结论在科学上仍有待商榷。相关研究仍然受样本数量、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限制,取样和检测方法也存在诸多干扰因素,类似对于微塑料的表征很可能夸大了微塑料的环境和人体赋存,从而陷入研究误区。
他指出,对于微塑料毒性机制,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与误区,微塑料的毒性靶点与分子机制尚不明确,容易推断出错误结论。
江桂斌表示,要重视新污染物的基础研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行动。研究者应当有更高的格局,对标来自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外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国家需求。